打开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打开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即可通过手机访问网站并分享给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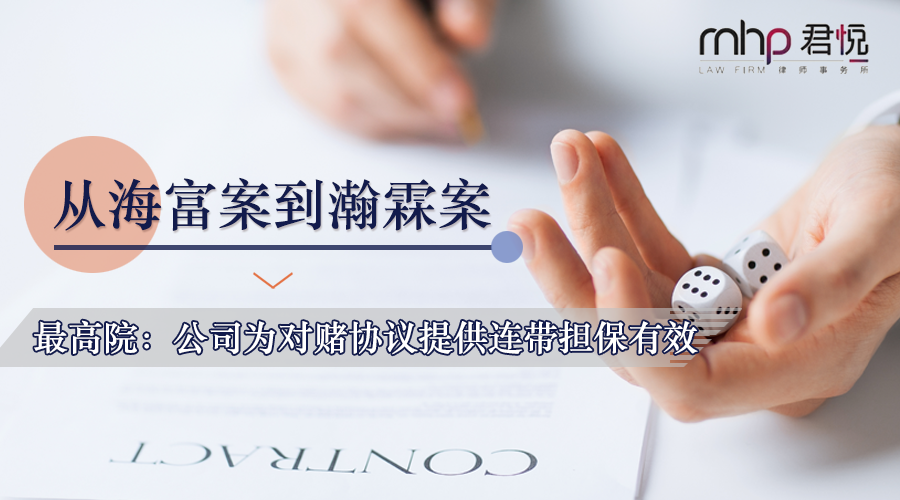
2018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强静延和曹务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作出再审判决[(2016)最高法民再128号](下称“瀚霖案”),认可融资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签署的对赌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有效性。

案情概述
2011年4月,投资人强静延以3000万元入股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瀚霖公司”),并与实际控制人曹务波约定对赌事项,即:如瀚霖公司未能在2013年6月30日之前实现合格IPO,强静延有权要求曹务波以现金方式回购强静延所持的瀚霖公司股权,回购价格为实际投资额外加每年8%的内部收益率,并由瀚霖公司为曹务波的回购义务提供连带保证。2012年5月,强静延与曹务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曹务波依据对赌协议回购强静延所持的全部瀚霖公司股权。然而,在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曹务波始终未履行回购义务。2014年4月,强静延又书面通知曹务波、瀚霖公司,要求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但始终未得偿付。
强静延遂将曹务波和瀚霖公司起诉至法院,并经一审、二审,一路上达最高人民法院。一审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二审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均判决强静延败诉,其核心理由皆与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判决的海富案[(2012)民提字第11号]中的思想一脉相承,即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认定该等约定“使[投资人]的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融资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而应当无效。但是,让众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最高人民法院却颠覆了海富案中确立的“公司对赌无效”的原则。
最高院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在瀚霖案中认定融资公司为对赌协议提供的连带保证有效,其论述理由主要包含如下两个层面: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淡化了瀚霖案中连带保证的对赌属性,而将纠纷焦点转向公司为其股东和/或其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成立要件。根据《公司法》第十六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因此,瀚霖公司连带责任担保的有效性应取决于担保事项是否已经通过股东会决议。就此事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瀚霖案中所涉主要交易文件均已声明瀚霖公司已通过相关股东会决议,批准本次交易各项内容,即包括瀚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的事项,因此认定投资人对担保事项的生效条件已尽到审慎注意和形式审查义务,进而担保条款对瀚霖公司有法律约束力。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又认为,退一步而言,即便担保事项未经股东会决议批准,但因为《公司法》第十六第二款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大股东滥用权力,而瀚霖案中的投资人将全部投资款均打入公司账户,供公司经营发展使用,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且瀚霖公司本身是最终的受益者,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十六第二款立法目的的情形,因此,无论瀚霖公司股东会是否就担保事项进行决议,该担保条款对瀚霖公司始终具有法律约束力。
只言片语
观察最高人民法院就瀚霖案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就公司对赌事宜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有意在(i)融资公司直接作为对赌协议一方的对赌方式(暂称为“狭义公司对赌”)与(ii)融资公司作为对赌协议一方担保人的方式(暂称为“广义公司对赌”)之间做一个区分。
在狭义公司对赌方面,除少数备受瞩目的仲裁判决以外,中国法院主要仍然延续着最高人民法院自海富案以来确立的“公司对赌无效”的原则。而就广义公司对赌而言,以本次瀚霖案为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淡化公司的对赌属性,以论证公司对其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法律成立要件是否已满足的方式,来确定广义公司对赌行为的有效性。如此处理巧妙地避免了直接讨论其在海富案中论述的“投资取得固定收益、收益脱离经营业绩、损害公司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观点,另辟蹊径认可了公司对赌的效力。
此外,我们也查询到,在瀚霖案之前地方法院曾就类似的融资公司为股东的对赌协议提供连带保证是否有效作出判决。例如,在上海立鸿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诉浙江中宙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34号](下称“中宙案”)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融资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未经股东会决议,因此该连带担保无效,判决投资人败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宙案,除了缺少股东会决议这一要件之外,上海一中院同时也补充道,“[对赌协议]内容实际会产生公司代其控股股东或其实际控制人承担债务责任的后果,亦即由公司承担[投资人]的投资补偿义务,故该约定有违公司法相关资本维持原则的强制性规定,同时亦会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的权益,故不应承认其效力”,可见,该判决仍未突破海富案确立的原则,即使经过股东会适当决议,中宙公司的连带担保责任还是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最后,从海富案到瀚霖案,我们不禁要问“狭义公司对赌”和“广义公司对赌”真的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别,以至于在两案中获得天壤之别的对待呢?如果对赌协议(或我们姑且俗称其对赌协议)本身就是一个投资领域广泛采用的机制,而海富案确定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中国的适用,从这一点来看,瀚霖案无疑是中国司法实践的一次进步,表明了中国法院对投资领域通行规则的进一步认可,以及对契约精神的尊重。